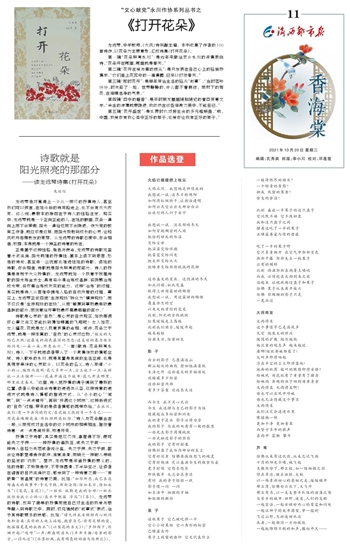龙远信
龙远琴绝对算得上一个从一而终的抒情诗人,甚至我们可以预言,在她今后的诗写路途上,也不会有太大改变。这么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诗人的性格注定。现实中,龙远琴就是一个正向正能的人,在她的眼里,花朵一律向上而不会萎谢,阳光一律灿烂而不会隐退。作为党的教育工作者,就应该是这样,把阳光投射到成长的心灵,让和风吹开每棵勃发的嫩芽。从龙远琴的诗歌态度中,你会相信,校园,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诗意的所在。
正是基于这种性格、角色与使命,龙远琴的诗歌充盈着汁液流淌、阳光明媚的抒情性,基本上读不到悲苦、愁绝的诗句,甚至连一丝忧郁也难进驻她的诗歌。读她的诗歌,你会相信,诗歌就是阳光照亮的那部分。诗人的抒情是有别于大众抒情的。龙远琴就如一个执意于挖掘诗歌的阳光炼金术士,具有将冷漠冶炼成温暖、将阴翳冶炼成光束、将疼痛冶炼成欢笑的能力。这种“冶炼”的过程,其实就是诗人从苦难中提纯人格的自我升腾的过程。事实上,龙远琴正试图把“生存现场”转化为“精神现场”,而不仅仅是“生存现场的在场”,从而“触摸到事物最柔软最温暖的部分,而刻意绕开事物最疼痛最晦暗的部分。”
诗歌是心灵的“自燃”,是心灵的自然现实,如我等满怀心事之流又怎能找到薄如蝉翼的飞翔呢?女人如花,女人懂花,花就是女人执意衷情的命相。或许,花朵之于远琴,就是一种本真的、“自燃”的心灵对应物。“枝尖的火焰已点燃/这最美的颜色最深的思念/这美丽的暴力炫目的闪电/一朵一朵,照亮永川。”一首《献诗:花朵照亮永川》,诗人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激情绽放的情感空域。诗人歌咏的永川,既是其置身其间的生活空间,也是其魂梦牵绊的心灵故乡。以花朵的名义,诗人写道:“小小的心,缄默而透明/花儿多开一点,尘土就少一点/美好就一点点铺开——/花朵开满这个城市/花儿开在哪里,哪里就是春天。”这里,诗人把抒情的调子调到了慢板的位置,读者从中能体会诗意的递进与从容,这种诗意的递进方式就是诗人情感的推进方式。从“小小的心”“缄默”,到“一点点铺开”,再到“开满这个城市”,这种渐进式的“自燃”过程,带来的是读者情感的同频燃烧。“在永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在花枝上找到另一个自己/——用花朵唤醒花朵/用红颜照亮红颜。”诗人与花朵融合在一起,从而完成对生活中的这个城市的相锲相生,推动着诗意一点一点浸润开来,弥漫开来。
抒情之于诗歌,其实是把双刃剑,拿捏得不好,便可能失之于傻——一种抒情的偏执狂,或失之于假——一种诗人自控力失范或者说泛滥。失之于傻、失之于假,都会让诗歌显得造作做作、油腻油滑,而缺乏一种耐人寻味的坚定的“内核”。显然,龙远琴是深谙抒情的要义的。她的诗歌,不矫揉造作,不夸饰圆滑,不浮华空泛,让读者在语言的自然流淌状态,感受到了一种诗意之美——“有筋骨”“有温度”的诗意之美。比如:“如你所愿,我已在这场盛大的战事中/手无寸铁,渐渐沦陷/仿如末日,仿如永生”(《菜花,菜花》);“一杯水 就取走我的全部/一杯水 就任由我小小的心/在水中飘摇 浮沉”(《茶》)。龙远琴的诗歌,放弃了简单的抒情而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融入到诗歌之中。同时,初见端倪的“叙事式”表达,给予其诗歌更多的质感。比如:“请允许我安顿好内心的闪电和沧桑/在你的土地上站起,抱紧自己/你有足够的爱,把摇摇晃晃的我扶正”(《以梨花的名义》);“夕阳西下,炊烟升起/“吱呀”一声/那扇明清木门半开半掩/母亲的影子,一闪而过”(《水墨松溉,我有明亮的词语与你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