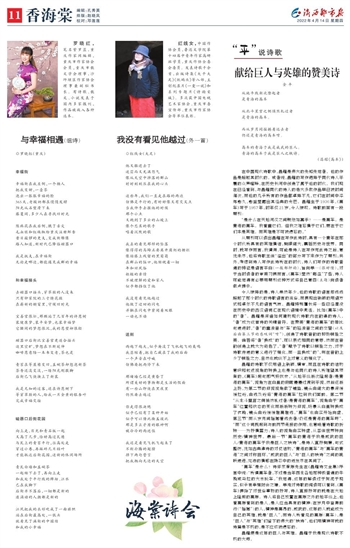金 平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
(昌耀《高车》)
在中国现代诗歌中,昌耀是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他的作品是超越其时代的。或者说,昌耀的写作迥异于同代诗人平庸的众声喧哗,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属于他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与昌耀同代的诗人的绝大多数作品早已被时间淘汰,而他的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卓异不凡,它们在时间中淬炼愈久,愈益显露出其经典的光芒。昌耀生于1936年,《高车》写于1957年,时年仅21岁,令人惊叹。诗歌前面有一段题引:
“是什么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是高车。是青海的高车。我看重它们。但我之难忘情于它们,更在于它们本是英雄。而英雄是不可被遗忘的。”
从题引可以读出昌耀在写作此诗时,具有一个青年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英雄情结,胸襟阔大,囊括历史与世界。同时,就写作而言,我猜测,可能是诗人在写作完此诗之后,意犹未尽,他将诗歌主体“溢出”的部分写下来作为了题引;另外,考虑到诗人写作此诗所在的时代,诗人们写作的诗歌普遍的特征是语言平白(一般都押韵)、旨向单一(很好懂),对于当时读者的审美习惯而言,《高车》显然“晦涩”了些,诗人可能觉得有必要用题引这种方式将自己意图(主题)向读者做点提示。
令人惊异的是,诗人虽然年少,他的诗歌的语言却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的诗歌语言的流俗,而展现出新颖的用语方式和卓尔不凡的语言气质。昌耀特别擅长将一些已经湮没在历史中的古汉语词汇在现代语境中激活。比如《高车》中的“者”。昌耀是深谙如何建构现代诗歌内在韵律的诗人,“者”成为这首诗的关键音符。在赞美“青海的高车”的排比句递进时,“者”的重浊音与“车”的轻浊音之间的交替(以及后面第三节的感叹词“呀”),创造了诗歌音韵的抑扬顿挫之美。倘若将“者”换成“的”,可以表达相同的意思,然而在音韵创造上就大为逊色了。“者”赋予了诗歌以顿挫之力,对于诗歌传递的意义进行了强化,而一旦换成“的”,则在音韵上少了顿挫之力,自然也就谈不上对意义的强化了。
昌耀的诗歌不仅用语上新颖、精审,而且在诗歌的结构意识和叙述视角的转换上也是与他同代的诗人所难望其项背的。《高车》起句即气势恢宏,“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视角为在白昼的俯瞰慢慢过渡到平视,然后逐渐上扬,为第二节的仰视视角做了铺垫,镜头由阔大的景深缓缓拉近,由远及近将“青海的高车”拉到我们面前。第二节“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视角由于“高车”位置和状态的变化而渐渐转为仰视,场景从白昼转换成了夜晚,镜头由近缓缓推高推远,“高车”也由实开始向虚。第三节“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而”这个词既起到与前两节连接的作用,也意味着诗歌的折转——为抒情蓄力;诗人的视角由实转虚,从客体世界转向历史/精神世界。最后一节“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是诗人直抒胸臆,句式整饬,犹如古典律诗的对仗结构,“青海的高车”与“高车的青海”之间对称回环,“威武的巨人”与“巨人的轶诗”之间的跳跃递进,充沛的情感在隐忍中的迸发尽在其间了。
“高车”是什么?诗评家燎原先生在《昌耀诗文全集》序言中说:“所谓高车者,不过是当年西北各地那种极普遍的牛挽或马拉的大木轮车。”我觉得,这样的解读过于拘泥于现实,似乎有牵强附会之嫌。单纯对诗歌的阅读可以看到,《高车》摒除了对世俗事物的抒写,诗人直接抒写的就是在大地上隆起的高原。诗人将自己放置在高原之外的地平线上,他看高原看到的是人,是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在岁月中奋勇前行(“摇撼”)的人,精神是高昂的、威武的,这样的人就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就是“巨人”,而诗人所看见的高原(高车),是“巨人”与“英雄”们留下的伟大的“轶诗”,他们用精神写就的诗篇是不朽的,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昌耀便是这样的巨人与英雄。昌耀于我是现代诗歌不朽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