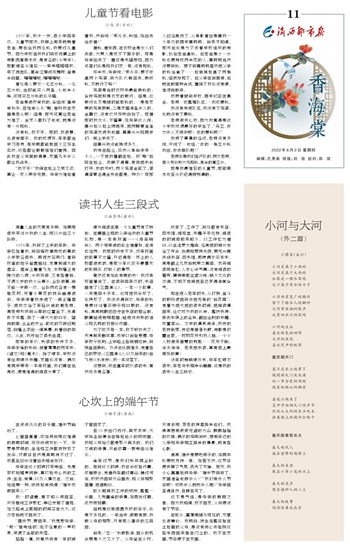◎施崇伟(渝北)
测量人生的尺度有多种。如果用读书来划分我的人生,可以分出三个阶段。
1974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拉扯着我,到旧庙改建而成的真武小学报名读书。跨进方石拱门,看到厅堂的柱子溜圆粗壮,支撑起阔大的屋梁。屋脊上雕着飞龙,木板墙上有隐约的人像,令我好奇,又有些害怕。不满七岁的我个头瘦小,台阶很高,尚不能一步跨一级。台阶两边各有一棵桂花树,开着小黄花的枝条垂得很低。母亲领着我走进了一间土墙屋子,把我交给了年轻俊俏的周老师。周老师引我到头排的位置坐下,木桌极不平整,裂了一道大大的口子。望向前面,土垒的方台,砌边的灰砖已脱落,白墙上漆出一道黑幕,斜着白的裂纹。从此,我开始了读书生涯。
那样的年代,所读的书并不多。母亲手缝的书袋,装着薄薄的两本书,《语文》和《算术》。除了课本,学校没有任何课外书籍,家里也没有。偶尔有同学带来一本连环画,我们围在他身边,便是难得的阅读分享了。
课外阅读在第一个儿童节有了转折。在镇里上班的父亲给我的儿童节礼物,是一本连环画——《海岛哨兵》。两个穿军装的战士端着枪,在海边站岗。我那时识字不多,对连环画的故事不太懂,只记得每一页上的人物都很威武,是那个年代孩子最喜欢的抓特务、打敌人的情节。
竟然还有如此有趣的书!我对连环画着迷了。在读到四年级时,书店里有了《三国演义》。一本一个故事,一共是四十多本。这可把我乐坏了,也馋坏了。我没法得到它,母亲的钱是要计划着买种子和口粮的。没有钱,常常就眼巴巴守在书店的柜台前,眼睛钻进玻璃柜里,钻进刘关张的结义和孔明的羽扇纶巾里。
为了收齐每一本,我下够功夫了。天亮起来割牛草,放学以后拾麦穗,母亲按斤收购;上学路上拾破铜烂铁,到废品店换钱。办法总比困难多,凭着自己的劳动,《三国演义》,以及后来的《岳飞传》《水浒传》,我一本没落下。
没想到,我在童年时代读的书,竟然好多是名著。
成年了,工作了,到处都有书店、图书馆、阅览室,书籍汗牛充栋,阅读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以工作忙为借口,以生活累为理由,经常把时间分发给了开会、饭局和荒废光阴,更无兴趣去逛书店、图书馆,即使偶尔买本书,常是翻上几页后就束之高阁。放弃阅读而奔忙,人亦心浮气躁;没有阅读的营养,精神常感空虚乏味;缺少文化的滋润,不知不觉间把自己变得油腻俗气。
现在进入老年时光,从打拼、奋斗的职场退回到与世无争的“后花园”,有着大把大把的读书时间,把阅读请回来,让它成为我的伙伴。整饬书房,抹去书架上的尘埃,翻出尘封的书籍,放置案头。文学的清泉润泽,历史的老枝新芽,传记是智者长廊,诗歌是初蕾含苞;一树树花开引我入胜,一个个人物递来智慧的钥匙……花开不断,流水缓缓。老来把书读,真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幼年时稀缺课外书,中年忙碌不读书,年老与书相伴乐融融,这是我的读书人生三段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