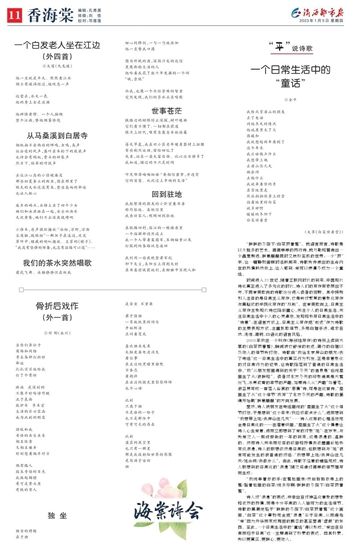◎金平
我给北京房山的朋友
去了电话
问他冬天的情况
他说屋里生了火
很暖和
我就想起新年要到了
这个年末
我应该做点什么
我想带上她
去房山住几天
她会问
去做什么
我说牵着你的手
在雪地里走
然后拍拍你身上的雪
指着地里的白菜
说多好啊
暖暖的冬阳下
白菜顶着雪
(大草《白菜顶着雪》)
“暖暖的冬阳下/白菜顶着雪”。就语言而言,诗歌是以少胜多的艺术。简简单单的两行诗,就勾勒和营造出一个晶莹剔透、暖意融融同时又质朴至极的世界;一个“顶”字,让一幅静物画顿时活跃起来,诗歌所传递出的生命内在的热情跃然纸上,让人感到:爱可以使凛冬成为一个童话。
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现代诗也真正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诗人们的写作探索层出不穷,不同审美取向的诗歌纷纷进入读者的视野。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常主义写作,它是针对繁复的意象化写作与高蹈式的学院化写作的“反叛”。在审美取向上,日常主义写作主张现代诗应降低重心,关注个人的日常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心灵律动,发现和书写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在语言方式上,日常主义写作把“叙述”作为诗歌的主要表现方式,注重抓取细节,多用白描手法,追求自然、洗练、简明、口语化的语言风格。
2003年我在一个叫作《原创性写作》的诗刊上读到大草的《白菜顶着雪》,瞬间被它舒缓的叙述、简约的白描以及动人的细节所打动。诗歌由“我给北京房山的朋友/去了电话”这一日常生活中的真实行为引发,正是非意象化的对日常行为的记录,让诗歌降落到了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的关于“冬天”的信息是“他说屋里生了火/很暖和”。读者对北方冬天的印象通常是大雪纷飞、冰寒彻骨的季节的严酷,如果诗人从“严酷”处着笔,很容易写成一首落入俗套的“悲情”诗,可是在这首诗,“屋里生了火”这个细节“改写”了北方冬天的严酷,诗歌的基调开始朝“暖意融融”的方向发展。
显然,诗人被朋友在电话里说的“屋里生了火”这个细节打动,于是想到“这个年末/我应该做点什么”,进而想到“我想带上她/去房山住几天”——诗人这样的心理活动完全是日常化的——在潜意识里,“屋里生了火”这个情景让诗人心生爱意,进而立即想到了爱的对象“她”:在岁末,与所爱之人一起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这是浪漫的、温暖的。然而诗人并未用炫目的修辞和抒情去浓墨重彩地书写这浪漫,诗人的联想依然是日常的,他联想到与“她”很有可能发生的很普通的对话:“我想带上她/去房山住几天/她会问/去做什么”。由此,诗歌不经意的铺垫完成,诗人联想到的日常化的“浪漫”随之将通过简单的细节描写而生成:
“我说牵着你的手/在雪地里走/然后拍拍你身上的雪/指着地里的白菜/说多好啊/暖暖的冬阳下/白菜顶着雪”。
诗人对“浪漫”的表达,并非出自对神圣化意象的想象和浓烈的抒情,而是十分平常的人人皆可为的生活细节,诗歌的高潮定格于“暖暖的冬阳下/白菜顶着雪”这个画面。“白菜”这个事物完全把“浪漫”系于日常,从而避免“爱”因为升华而变成瑰丽的飘忽的甚至显得“虚假”的东西。至此,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童话”得以形成,“爱出自日常而归于日常”这一主题得到了朴素的表达。因其朴素,所以更真实、更暖心、更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