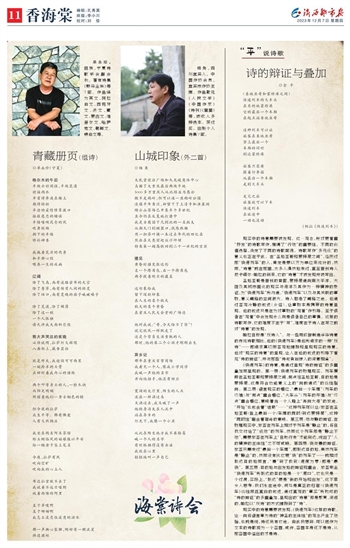◎金 平
(圣地亚哥和蒙特港之间)
快速列车的火车头
在目的地蒙特港
它的最后一个车厢
在起点站圣地亚哥
这种列车可以让
旅客在圣地亚哥
登上最后一个
车厢的同时
到达蒙特港
旅客只需要
提着行李箱
从最后一个车厢
走到火车头
走完之后
旅客就可以下车
快速列车
在旅途中
一动也没动
(帕拉 《快速列车》)
现实中的诗意需要被发现。这一观念,针对更看重“抒发”的诗歌写作,强调了“行动”的重要性。不同的价值选择,决定了不同的诗歌面貌。诗歌写作“多元化”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圣地亚哥和蒙特港之间”,经历过那“快速列车”的人,肯定是要以万为单位来统计的,然而,“诗意”就在那里,太多人漠然地走过,直至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的到来,它的“诗意”才被发现并被写出。
圣地亚哥是智利的首都,蒙特港通向南太平洋。大陆及其城市固化的现实与海洋及其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为“快速列车”所沟通。“快速列车”以及与其关联的事物,意义阐释的空间很大。诗人拒绝了阐释之途。他通过客观冷静的叙述(介绍),让事物本身携带的诗意呈现。他的叙述只是在为对事物的“观看”作引导。至于读者在“观看”中会发现什么则是读者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诗歌写作,它的难度不在于“写”,难度在于诗人在写之前对“诗意”的发现。
帕拉自称是“反诗人”。与一些用修辞制造浮华诗意的传统诗歌相比,他的《快速列车》是他所追求的一种“反诗”——即追求真切而客观地捕捉和呈现现实的诗意。他对“现实的诗意”的呈现,让人在他的叙述的引导下看见“诗的辩证”,并与那些“诗句背后惊人的深意相逢”。
《快速列车》的诗意,是通过呈现“诗的辩证”的多重叠加而呈现的。第一层:快速列车的物理现实。列车横跨在圣地亚哥和蒙特港之间,起点站圣地亚哥,目的地是蒙特港,这是符合功能意义上的“向前通达”的线性指向。第二层:语言现实的错位。“最后一个车厢”(列车的终端)与“起点”重合错位,“火车头”(列车的开端)与“终点”重合错位,意味着当一个人踏上“奔向大海”的旅途,“开始”也包含着“结局”——“这种列车可以让/旅客在圣地亚哥/登上最后一个/车厢的同时/到达蒙特港”,这种“同时性”暗含着宿命的意味。第三层:动与静的辩证,在物理现实中,旅客在列车上相对于列车是“静止”的,将自我交付给了“运动”的列车,然而这个列车却是“静止不动”,需要旅客在列车上“自助行走”才能到达,说出了“人的精神的主体性”之不可或缺。第四层:快与慢的辩证。旅客只需走过“最后一个车厢”,即抵达目的地,虽然列车是“静止”的,然而没有比它更“快”的列车了——就相对抵达目的地而言,“慢”到了极致(速度为零)即是“最快”。第五层:目的地与出发地的辩证和重合。旅客乘坐“快速列车”所抵达的目的地是一个“港口”,它也只是一个过渡,实际上,“抵达”便是“新的开始和出发”,这不禁令人思考:我们永在途中,何处是真正的归宿?《快速列车》线性而且直白的叙述,通过直观的“事实”所构成的“诗的辩证”的多重叠加,呈现出的“诗意”却是繁复、深邃的,帕拉以“反诗”的方式捕捉到了“诗”。
现实中的诗意需要被发现。《快速列车》这样的诗歌,让一向将语言奉为诗的“神圣的主体性”的观念产生了动摇,也就是说,诗还另有它途。由此我想到:可以把作为文本的诗歌视为一个容器,或许,容器本身还不是诗,从那容器中溢出的才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