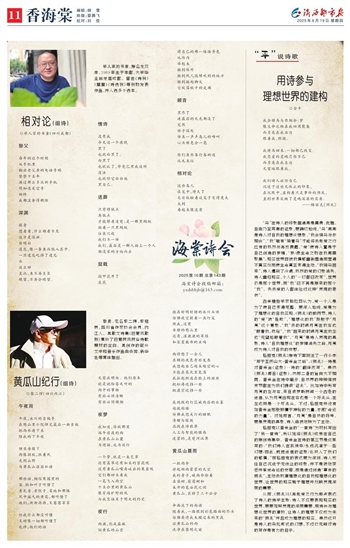◎金平
我会骑马与你相会:梦
像生命之物在我四周聚集
而月亮在我右边
跟着我,燃烧。
我骑马回来:一切都已改变。
我恋爱的灵魂悲伤不已
而月亮在我左边
无望地跟着我。
我们诗人放任自己
沉迷于这些无休止的印象,
在沉默中,虚构着只是事件的预兆,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深层的需要。
——格丽克《预兆》
“马”在诗人的印象里通常是高贵、优雅、自由乃至英勇的征象;更确切地说,“马”常常是诗人对自我的理想化想象。“我会骑马与你相会”,“我”唯有“骑着马”才能将去赴爱之约应有的热烈与奔放展露。“爱”使诗人置身于自己创造的梦境,“梦/像生命之物在我周围聚集”,现实世界因被我情感重新塑造而显得不真实反而使生命真正变得生动。“我骑马回来”,诗人遭到了冷遇,热烈的爱的幻象消失,诗人重归现实,个人的“一切都已改变”,世界仍是那个世界,而“我”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失去爱的人都体验过这种“灵魂的悲伤”。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爱一个人是为了使自己变得完整。更深入地说,爱是为了理想化的自我实现。《预兆》的前两节,诗人的“爱”被“挫败”,“理想化的我”投射于“月亮”这个意象,“我”去的时候月亮在我右边“跟着我,燃烧”,“我”回来的时候月亮在我左边“无望地跟着我”。“月亮”是诗人灵魂的具象,诗人“自我理想化”的梦境消失之后,月亮成为诗人对自我的安慰。
格丽克《预兆》原诗下面附注了一行小字“写于亚历山大·普希金之后”。《预兆》一诗是对普希金《征象》一诗的“翻译改写”。虽然《预兆》源自《征象》,然而二者的旨向大不相同。普希金在诗中暗示,自然界的种种细枝末节都在为我们提供“征兆”。比如诗中所写月亮的左与右,来自俄罗斯民间一个古老的迷信,认为月亮出现在右边是一个好兆头,在左边则是一个坏兆头。不过,格丽克并没有如普希金那般服膺于神秘的力量,亦即“命运的力量”。对她而言,“月亮”是自然的符号,更是灵魂的具象,诗人由被动转为了主动。
格丽克以普希金的“一首诗”为材料写出了“另一首诗”,所以她将《预兆》收录在自己的原创诗集中。普希金在诗的第三节是这样写的:“我们诗人在孤独中/永远沉湎于一些幻想/因此,就把迷信的征象/也织入了我们的感情。”而格丽克的表达更为深刻,诗人放任自己沉迷于无休止的印象,并不是被动获悉并承受命运的安排,而是通过创造“事件的预兆”,主动去构建理想化的自我和理想化的世界,让世界的现实趋于理想并反映灵魂深层的需要。
从而,《预兆》以奔赴爱之约为起点表达了诗人的诗学主张:诗人不仅要表现现实的世界,更要观照灵魂的深层需要,用诗参与理想化世界的建构,让诗人的理想不仅成为未来的“预兆”并且成为理想的现实。虽然这只是诗人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不过它无疑对诗的写作是有力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