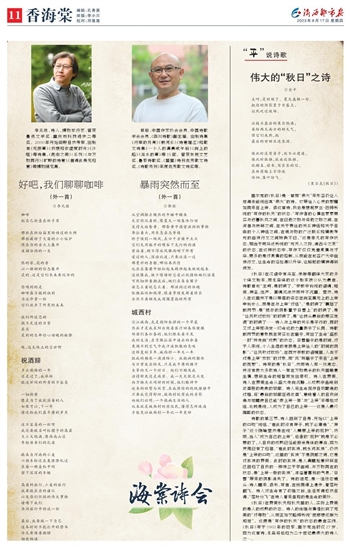◎金平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
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
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里尔克《秋日》)
里尔克的《秋日》是一首用“伟大”来形容仍让人觉得未能说出其“伟大”的诗。它带给人心灵的慰藉如同来自上帝。读这首诗,我总是想起罗兰·巴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的状态:“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与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这是非凡的写作状态,相当于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写作不仅仅凭借激情与才华,更多的是对激情的控制,从而能在包容广大中幽独行文,让生命的经验得以升华,让超越的精神得到迸发。
《秋日》在汉语中有冯至、绿原等翻译大家的多个译文版本,而北岛译的这个版本被公认为最佳。诗歌首句“主呵,是时候了。”宗教中诉说的语调,短促,神圣,庄严。基调沉淀然而并不沉重。显然,诗人在这里并不是以卑屈的姿态在向至高无上的上帝申诉什么,而是在与上帝“对话”。“是时候了”囊括了前两节:是“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的时候了,是“让风吹过牧场”的时候了,是“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的时候了……诗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平行的,同时又对上帝那决定一切命运的力量表示了认同。诗歌前两节的意象既在写实也在暗示,写出了生命“盛极一时”并走向“成熟”的状态。日晷暗示的是时间,对于人来说,个人生涯的有限是上帝给人的“时间的阴影”;“让风吹过牧场”,在西方宗教的语境里,人类不过是上帝“放牧”的对象,而“风”则暗示了来自“上帝的抚慰”。诗写的是“秋日”,然而诗人却一反常态,并没有像大多数诗人一样在万物肃杀的秋天里触景生情,想到生命的短暂而发出悲叹。诗人在赞美。诗人在赞美生命从盛大走向沉静,从成熟中品味到浓酒般的微微的甘甜。诗人将生命视作自我酿造的过程,将“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意味着人的自我创造与觉醒使自己能“像上帝一样”与“上帝”平等地对话,也就是说,人成为了自己的上帝——这是人最终陶醉的状态。
诗歌的第三节,诗人回到了自身,开始以“上帝的口吻”说话。“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房子”这个隐喻显然是在说“人需要上帝的庇护”,然而,当人“成为自己的上帝”,他者的“庇护”就是不必要的了,人自我的成熟已经能接受身体的漂泊,因为灵魂已有了归宿。“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仍然是“上帝的口吻”,这里的“孤独”不是阴郁之词,它是对孤独的赞美。此时的孤独,是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回归了自我的一种独立于宇宙间、与万物同在的状态,是“上帝一般的孤独”,洋溢着喜悦的气息。“日晷”带来的阴影消失了。诗的结尾,是一组动态镜头:诗人醒来,读书,写信,在林荫道上漫步,看落叶翻飞。诗人对生命有了彻悟之后,生活变得悠然自得,“落叶纷飞”在诗人看来呈现的是生命的美妙。
《秋日》在赞美秋天和秋天里的人,实际上赞美的是人的成熟的状态。诗人的体悟与情绪找到了完美的“对等物”,从而正如艾略特所说“把思想还原为知觉”。这便是“写作的秋天”的状态的最佳实例。《秋日》写于1902年的巴黎,里尔克当时仅27岁。因为这首诗,北岛将他归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