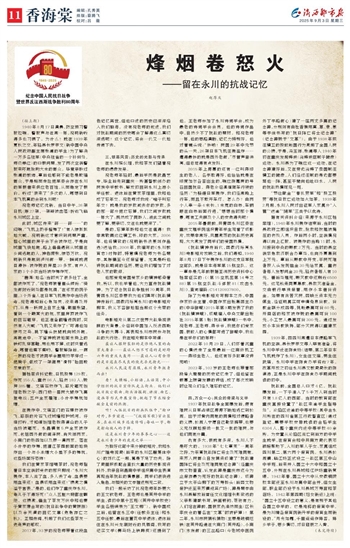赵厚庆
(接上期)
1940年8月17日清晨,防空预习警报拉响。警报声与往常一样,况明新听得多也习惯了。为什么?就在1939年夏秋之交,年轻县长罗宗文(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的学生)为了解决一万多名驻军(中央驻省的一个补训处,师级单位)的口粮问题,发了两次空袭警报来吓跑抢购大米的群众。毕竟亲聆过张澜的教诲,事后他感到不能老是欺骗群众,于是铤而走险把军委会存在永川的军粮借来供应老百姓,从而稳定了粮价。听过“狼来了”多次的人,哪想到日本飞机真的会到永川呢?
况老师记忆犹新。当日中午,26架日机(原27架,一架疑被击落)折返飞临永川城区上空。
此时,城区传来“砰……砰……”的闷响。“飞机上扔手榴弹了!”有人惊抓抓地大喊。况明新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担心城里的房子会不会被炸烂,于是向城里飞快地跑,路上偏偏遇到从城里往乡间逃跑的人,神色慌张,惊恐万状。况明新只身跑到泸州街一带,一瞬间就满目凄惨:被炸毁的房屋20多家,有户人家的3个小孩当场被炸弹炸死。
“唐湾(地名)当时关了很多壮丁,全都被炸死了。”况老师皱着眉头倾诉:“骑龙街附近到处都是坑洞。”在邻家的院子里,3个外省人在日军飞机轰炸中当场丧命,况老得知后心急如焚,没来得及开门,纵身一跃爬上自家土墙,朝里张望,看到一个簸箕大的坑,家里房顶被炸飞的巨石砸穿。他正准备翻墙进院时,突然有人大喊:“飞机又来炸了!”吓得他如惊弓之鸟,跳下墙头拔腿就向城外跑。奔跑途中,一不留神就被地面木块上的铁钉扎穿草鞋,甩也甩不掉,这时只管逃命,哪管他痛不痛哟。警报解除后,一瘸一拐的况老才被同学余雷用竹竿穿过一把椅子,做成了一架简易“滑杆”抬回殷家巷的家。
据档案资料记载,日机投弹129枚,炸死155人,重伤86人,轻伤183人;毁房385幢。文庙石坊炸飞,碎片砸死饭馆老板之子;西门坳一居民大腿炸飞高挂电线;五户全家罹难;小什字弹坑如塘。
在轰炸中,文庙正门的石牌坊被炸飞,碎裂的片石飞过城墙和护城河。仔细打听,才知道饭馆老板蒋德山的儿子当场被砸死。永昌镇有5户全家被炸死,包括西外街的阎泽民、肖天祥两家,小南门的杨四如以及廖一清两家。落在小什字的炸弹,把福江茶园前面的地块炸出一个与小池塘大小差不多的弹坑。这些场面好恐怖!
我们在黄家茶馆喝茶时,况老师指着日本空袭时受伤的那只脚说:“永川大轰炸,本人流了血,多人丢了命,血债要用血来还!血债该用血来还!”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是的,他们炸了重庆炸永川,龟儿子不得好死!”众人五脏六腑都在颤动。这愤激,催生了茶友万俊中和他妻子黄家婕合写的《抗日战争中的黄振刚》以及余天潢的回忆文章《危急存亡之秋》。互相传阅,引起了我们这些茶友一迭连声的感叹。
2017年,93岁的况老师带着这段血色记忆离世,但他口述的历史已深深烙入我们脑海。没有况老师的叙述,我们对抗战期间的历史哪会了解得这么真切深透呢?这个记忆,将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三、银幕风雷:历史的光影与传承
在永川殡仪馆,我和茶友们望着况老师的遗像发呆。
况老师年轻时,最后学历是武昌艺专,毕业后先到重庆一所基督教创办的民族中学教书,解放初回到永川上游小学任教。退休后在黄家茶馆里,我和他成了忘年交。况老师对我说:“啥子叫忘年交?就是我的岁数减去你的岁数,多的那一部分把它忘掉,我们之间岁数就一样大了;既然成了同龄人,彼此之间就更了解,更亲切,交往也就更深了。”
是的,忘掉年龄和他交往值得!我非常敬佩这位精工书、印的大家。2006年,他将精致的《况明新书法篆刻作品选》送给我;2008年,我编写的《永川教育志》付梓时,特意请况老师为书名题字,其原稿至今还保留着。尤其是听他讲抗战期间的经历,更让我们增加了对老人家的敬仰。
他那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精神感染着我,所以,我也学着他,大力宣传抗战精神。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共青团永川区委要我为他们撰写《抗战精神传后代,团徽闪烁亮永川》的电影短片脚本,我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光荣的任务。
电影短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枭视狼顾的大背景,介绍到中国加入反法西斯斗争的大搏斗,再表现永川市民参与抗战的大行动。我在短片脚本中写道:
最让人摧肝裂胆的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最让人怒不可遏的是时跨六年的重庆大轰炸……最让人心有余悸的是日寇丧尽天良的烧光杀光抢光……
永川人民没有屈服,永川青年挺身而出!
看!大横幅,小标语,土话筒,中小学组织的抗日宣传队走上街头。他们以抗日救亡歌曲、街头活报剧、讲演、曲艺、漫画等形式开展宣传,掀起了节衣缩食献金支前的热潮。
听!入伍抗日的新兵队伍中,“枪口对外,齐步前进……”《救国军歌》穿云裂石,在永川城乡迅速传唱;每吐一字,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
这是永川青少年的拳拳之心……这是永川青少年的虎虎之举……
为拍好这部十来分钟的短片,我和永川广播电视局(后来的永川区融媒体中心)的刘代江一起,算是下足了功夫。除了局里积极配合查找大量的历史影视资料外,我亲自到昌南中学组织高中生表演再现当年抗战的情景剧。同学们很快进入角色,与相关的文字描述别无二致。
我们一起采访了比况老师年龄更大的王文钦老师。王老师也是英井中学的学生,读初中第十五班(《英井中学校史》学生名册误录为“王文卿”)。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永三中(任教务主任)和永五中任教,最后在萱花中学退休;退休后住在永川兴龙湖附近的凤栖阁,我写的纪实文学《赛马场上铁蹄疾》还提到了他。王老师参加了永川诗词学会,成为最老的诗词学会会员。他的诗词作品中,自然少不了抗战的题材。和况老师一样,他的思路清晰,记忆力特别好。他对着镜头说:“惨呐!民国29年中元节的头一天,26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遭得最惨的就是西外老街。”尽管声音洪亮,但总觉得有点发抖。
2015年上屏幕的还有一位叫蒋印生的老人。名字取得好,他恰恰就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生的,响应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日。蒋老介绍滇缅驾车行驶的经历:“为躲避日军轰炸,我们经常晚上行车,而且不敢开车灯。怎么办?由两个人牵一条4米长、1米宽的白布,车辆跟在白布后面行进。”想想当时那个情景,哪有工夫顾及个人的安危得失呢?
2015年暑假前,共青团永川区委在重庆文理学院组织青年学生观看了该影片,效果非常好,风雷激荡的抗战历史再现,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抗战精神传后代,团徽闪烁亮永川》电影短片放映之后,我们得知,1940年8月17日下午轰炸永川的这支日军航空部队,就是日本海军第15航空队。这一事件是几年前根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证实的:《(第15空机密第14号之88)第15航空队战斗详报81(攻击永川)》,查询编码:C14120937800。
除了为电影短片写脚本之外,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中华辞赋》2015年第9期发表了我的《抗战精神赋》,该赋编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版《抗战精神赋》一书中。况老师、王老师、蒋爷爷,我把你们爱家国、恨敌人的心情都写进了辞赋中,我也是在学你们的样呀!
2022年10月29日,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走了全球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老人。他还有好多故事没讲完呐!
2023年,102岁的王老师也带着那段烽火腾腾的历史记忆走了,但他留在银幕上振聋发聩的讲话,成了每次放映时让观众们经久难忘的记忆。
四、万众一心:民众的脊梁与义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便有难民从日军占领区源源不断地逃亡到松溉。出于对骨肉同胞的同情和对侵略者的义愤,松溉人宁愿自己勒紧裤带,也要义无反顾地接纳一批又一批的难民,与他们同袍分羹。
仇有多大,恨就有多深。永川人不是吓大的。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为祭奠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来苏人民群众自发捐资修建了“抗战建国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纪念碑”(经重庆市文物普查,认定此碑是重庆市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抗战纪念碑)。该碑立于太平山脚下的万寿桥头(后因文物保护迁至来苏镇迎宾广场),碑身题字由永川县解放后首任文化馆馆长彭致远的父亲彭建猷书写,铁画银钩,苍劲有力。人们站在碑前,国恨家仇油然而生(区长李庆仓的署名在“文革”时被铲掉)!第二年,永川市民捐钱捐物(主要是破铜烂铁)在英井路通往大南门(英井路)、小南门(木货街)的三岔路口(今老城中医院外丁字路街心)建了一座两丈多高的纪念碑,分别刻有由杜香樵用真、草、隶、篆等字体书写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毁于“文革”)。由于1938年底汪精卫的投敌叛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于是,冯玉祥、张澜等人1940年初在重庆发起铸逆(浇铸逆臣贼子跪像)运动。永川县为了响应这一运动,在纪念碑建好后,又在旁边浇铸了卖国贼汪精卫的跪像,人们经过汪贼的身边都要骂他一阵,甚至干脆向他吐口水。人民的抗战热情可见一斑。
“节俭献金”“春礼劳军”和“投工投劳”等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1939年2月起,永川人民对出征军人家属分“入营”“送渝”“随军”三类予以优待。
据有关资料介绍(来源于永川区档案馆),1940年永川轰炸结束后,当时的县政府立即组织自救,抢救和挖掘被掩压的伤残人员。炸后两小时,空袭情况得以向上汇报。被轰炸的当晚11时,永川接到中央的赈款2万元。当时的县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也向外募集到上万元。事后从赈款中开支,平民死难者按人头发抚恤金30元给家属。重伤者每人发慰问金20元,轻伤者每人有10元。善后处理完,赈灾款中还剩近6500元。这笔钱连同募集款、县救灾准备金,交由银行单独保管,用作小本借贷资金。如果有贫苦灾民,因缺乏资本无力谋生,经证明属实可申请免息贷款。贷款金额分成四等,挑贩最高可贷60元,开商店的和家被炸毁的最高可贷100元,小工艺人最高可贷300元。通过发放小本贷款扶持,部分灾民得以重建家园。
1939年,因四川常遭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空袭,县长罗宗文等人早有准备,将永川中学迁往陈食场(结果,第二年日本飞机就炸了永川),女生住文庙,男生住武庙。永川中学在陈食办学将近7年。改革开放之初任永川县文教局局长的陈德沛,正是永川中学在陈食办学期间就读的初中。
抗战前,全国总人口才4亿。抗战爆发后,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到当时只有1.8亿人的西部。当时的教育部在重庆直接设置了“战区来渝学生指导处”。沦陷区迁渝的中等学校(其中含永川所在的四川省第三行政督查区)通过登记,需要学校安排就读的合格学生6304人,整个重庆内迁中等学校40余所。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在保育会和中共南方局代表邓颖超帮助下,入川的军人子女、家属组成四川第二、第六两个保育院。永川县松溉镇、临江场正式设立一战区第三中山中学班,后来并入国立十六中和国立十五中,分别在永川县城和红炉场重新复课。1942年春,国立十六中从安徽铜陵校本部迁至永川与高中部合并,但女生部、职业部仍设于永川县城万寿宫和茶店场。1942年第四期《妇女新运》上说:“国立十五中设立的意义,是有别于其他各国立中学的。它是纯粹的保育中学,是为川境各保育院新升学的保育生而新设的。”月光如霜,千里迢迢作异客。异乡学子,思乡情切,对日寇恨之入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