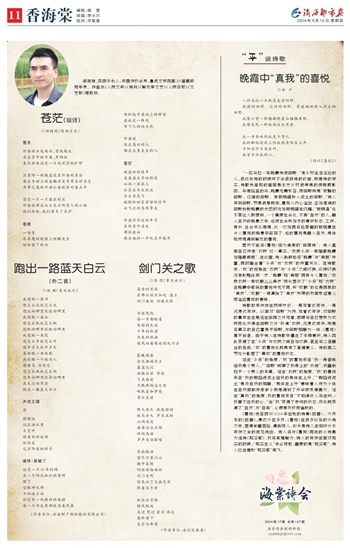◎金 平
一匹马拉一车晚霞走进田野。
寂静的田野。辽阔的田野。有玻璃碴掺入泥土的田野。
我像小资一样播撒晚霞如播撒粪肥,
我像农民一样收割丛丛黑夜。
我一身香味但我是个男人。
我的脚陷进泥土但我的身体在上升。
不知道什么鸟在叫,
我管不住我的心。
(西川《喜悦》)
“一匹马拉一车晚霞走进田野。”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读这句诗的时候并不会读到诗的修辞,而是诗的写实,诗歌所呈现的画面是北方乡村很寻常的傍晚剪影图。马是轻盈的马,晚霞无需形容,而田野则是“寂静的田野。辽阔的田野。有玻璃碴掺入泥土的田野。”诗人写到田野,节奏很是明快,喜悦从内心溢出,正如湿润的田野折射晚霞的光芒时犹如玻璃碴在闪耀。“玻璃渣”也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高度社会化、不再“自然”的人,融入自然的晚景之中,他被社会所加予的意识形态、工作、身份、社会关系等等,这一切如同将他禁锢的玻璃罩在令人喜悦的晚景中碎裂了,他的喜悦是融入自然、身体和灵魂得到解放的喜悦。
显然不能将《喜悦》视为通常的“田园诗”。诗人直面自己并非“农民”这一事实。“我像小资一样播撒晚霞如播撒粪肥”,在这里,诗人新颖地将“晚霞”与“粪肥”并置,同时暗含着“小资”与“农民”的并置关系。在诗歌中,“我”的视角在“农民”与“小资”之间切换,这种切换没有贬黜任何一方,“晚霞”和“粪肥”同样令人喜悦,“我像农民一样收割丛丛黑夜”则也显示了“小资”和“农民”在晚霞中感到的喜悦并无不同,所“收割”的也是同样的“黑夜”,“收割”一词清除了“黑夜”所带的负面象征意义而溢出喜悦的意味。
诗歌的写作存在两种方式:一是观看式写作,一是沉浸式写作。以面对“田野”为例,观看式写作,对田野的摹写往往是站在田园之外观看,即便将自己想象为农民那也只是在田野之外“扮演”农民;沉浸式写作,则是将真实的自己置身于田野,与田野相融为一体。《喜悦》属于后者。由于诗人在诗歌中灌注了平等意识,诗人因此获得了在“小资”与农民之间自如切换、甚至将二者融合的自由,“我”的喜悦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诗的第二节充分彰显了“真我”的喜悦状态。
站在“小资”的角度,“我”的喜悦来自“我一身香味但我是个男人。”“田野”卸掉了我身上的“伪装”,我重新归于一个男人的本真。站在“农民”的角度,“我”的喜悦来自“我的脚陷进泥土但我的身体在上升。”“脚陷进泥土”是与自然的相融,“身体在上升”意味着人作为个体在自然面前并非渺小而是得到了升华而变得高大。站在“真我”的角度,我的喜悦来自“不知道什么鸟在叫,/我管不住我的心。”当“我”获得了赤诚的状态,我也就获得了“自然”与“自由”,心便是欢欣而雀跃的。
《喜悦》选自西川2024年出版的诗集《巨兽》。大开本的《巨兽》,厚达六百多页,《喜悦》在很多驳杂的大诗之中,显得举重若轻、清新可人,似乎是诗人在知识分子写作之余的闲笔逸出。诗人将与《喜悦》同类的小诗集为组诗《现实感》,我将其理解为:诗人的写作在面对现实的时候,“现实主义”未必可取,重要的是“现实感”,诗人应当借助“现实感”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