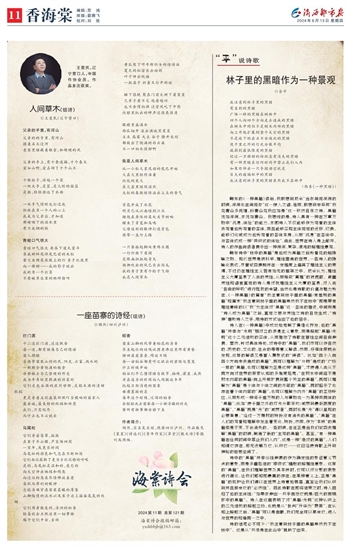◎金平
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
有差别的黑暗
广场一样的黑暗在树林中
四个人向四个方向走去造成的黑暗
在树木中间但不是树木内部的黑暗
向上升起扩展到整个天空的黑暗
不是地下的岩石不分彼此的黑暗
使千里之外的灯光分散平均
减弱到最低限度的黑暗
经过一万棵树的转折没有消失的黑暗
有一种黑暗在任何时间中禁止我们入内
如果你伸出一只手搅动它就是
巨大的玻璃杯中的黑暗
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虽然我不在林中
(韩东《一种黑暗》)
韩东的《一种黑暗》读后,我联想到尼采“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这一惊人之语,继而,联想到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一欣然自足之诗。黑暗犹如深渊,亦犹如青山。我想说的是,诗人具有一种在万事万物中“沉浸、体验”的能力,亦即诗人不仅能够作为观看的主体去观看他所观看的客体,而且能够实现主体视觉的迁移、切换,能够幻化或成为他所观看的客体本身,从而“沉浸”在客体中,与客体达成一种“共识式的体验”,由此,世界在诗人身上敞开,诗人的作品向读者展示出一种渊深、复杂、混沌的超理性景观。
韩东诗中“林中的黑暗”是他成为黑暗之后所看见的超隐喻之物。现代世界是被科学、理性塑造的世界,一些诗人的隐喻化表达,尽管试图摆脱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理性主义的束缚,不过仍在理性主义若有如无的框架之中。尼采认为,理性主义大厦窒息了人类的灵性,从而导致“真理”的被遮蔽。倚重灵性和语言直觉的诗人是对抗理性主义大厦的窒息,对人类“自由的呼吸”进行拯救的希望,当然也是诗歌的价值与魅力所在。《一种黑暗》的篇首“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有差别的黑暗”和篇末“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虽然我不在林中”即是带有理性意味的以“我”为主体对“黑暗”这一客体的描述,中间则是“诗人成为黑暗”之后,直觉之思与灵性之诗的自动生成,“诗神”借助诗人之手,用诗的方式给出了他的启示。
诗人在《一种黑暗》中成功地克制了情绪化抒发,他的“黑暗”并非与“光明”相对立的浪漫主义意象,而是超越“黑暗/光明”这个二元结构的实体,从而推动了诗歌在智性空间自由伸展。显然,针对具体诗句,对诗中的“黑暗”,我们尽可以作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意义解读,然而,仔细体察就会发现,这样的解读又是盲人摸象式的“误读”。比如“四个人向四个方向走去造成的黑暗”,既可以理解为“分歧”造成的“广场一样的”黑暗,也可以理解为正是这种“黑暗”,才使得人类从不同方向对世界的探索认知的多角度拓宽;“在树木中间但不是树木内部的黑暗/向上升起扩展到整个天空的黑暗”,既可以理解为“黑暗”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外部的“黑暗”,同时昭示了也存在着个体内部的“黑暗”,也可以理解为内外“黑暗”的互动呼应,从而形成一种将千差万别的人与事物统一为某种共同体的“黑暗”;比如“使千里之外的灯光分散平均/减弱到最低限度的黑暗”,“黑暗”既是“光”的“减弱者”,同时也是“光”得以呈现的必要背景;“经过一万棵树的转折没有消失的黑暗”,“黑暗”在人们的观看和理解中发生着变化、转折,然而,作为“本质”的黑暗却是不变、不会消失的,一些时候,往往正是当我们试图去理解“黑暗”的时候,制造了新的“主观的黑暗”。甚至,“有一种黑暗在任何时间中禁止我们入内”,这是一种“绝对的黑暗”,人们知道它存在,却无法触及它、认识它——这已经使诗歌上升到神秘的哲思空间了。
诗中的“黑暗”并非线性伸展的作为确定性的象征意义节点的意象,而是多重扭结的“悖谬式”辐射的超理性意象。这样的“黑暗”,在我们理解世界及其本质时,它可以对纷繁的表象进行简化,让我们感知那最高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黑暗”的庇护让我们得以在世界上诗意地栖居,直至让我们认识到并且接受它的“必然性”。因此诗歌在即将结束之时,诗人回归了他的主体性:“如果你伸出一只手搅动它就是/巨大的玻璃杯中的黑暗”。诗人在这里表明了对“黑暗/光明”这种认识上的二元结构的超越立场,也就是从“批判”升华为“赞美”,在认知上超越之后,“黑暗”可以是佳酿,我们完全可以享受它,进入与世界的和谐同一之中。
诗的结尾必不可少:“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虽然我不在林中”。这是从“只缘身在此山中”跳跃了出来。